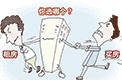隱藏在上海里弄里的“癌癥旅館”。
癌癥患者和家屬聚集蝸居醫(yī)院周邊 上海正嘗試將小醫(yī)院80%床位轉(zhuǎn)為護理床位
上海租房生意最好做的幾個地方中,一定會有醫(yī)院的身影。不少背著沉重行李的患者和家屬,正是看中這里相對優(yōu)質(zhì)的醫(yī)療資源趕來,而醫(yī)療資源的緊缺加上巨額的醫(yī)療開支,讓這些患者和家屬只能“蝸居”在醫(yī)院周圍。人們把這些出租屋叫做“癌癥旅館”。
不僅是上海,這種情形在每個大城市里都很常見。目前,上海市政府正嘗試將小醫(yī)院80%的床位轉(zhuǎn)為護理床位,幫助術(shù)后患者能在醫(yī)院得到護理,但床位似乎仍供不應(yīng)求。近日,本報記者走訪上海一些患者和家人集中居住的小區(qū)和里弄,探訪“癌癥旅館”。
遇到王詠梅時,她正趕回自己的出租屋做飯。王詠梅來自安徽,為了陪伴患病的母親,已經(jīng)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。這一年多的時間里,王詠梅就一直生活在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。
看病:住再差,能省就行
在上海,像王詠梅住的這種在老式里弄、沒有獨立衛(wèi)生設(shè)備、用板房結(jié)構(gòu)建造的小屋子被稱作“亭子樓”、“灶披間”,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,大部分上海普通市民都居住在這樣的小樓里。然而,隨著近幾年房地產(chǎn)開發(fā),城區(qū)原有的居民大多搬遷,醫(yī)院周邊未被拆除的“灶披間”不經(jīng)意間成了“搶手貨”。
以王詠梅的這間“灶披間”為例,每天炒菜做飯使用的都是走廊的公共廚房,每個廚房如同迷你的格子間一般,油煙把墻壁都熏黑了。而樓里唯一一個衛(wèi)生間要服務(wù)十余戶人家,所以每家每戶還是需要用最原始的馬桶解決生活問題。這樣一間租屋,每月租金也要1000元以上。
“到上海來看病,什么都要花錢,所以能省就省吧”。中午,王詠梅給自己準備的午餐是面條配窩窩頭,“下午還要趕到醫(yī)院去照顧母親。家里一共3個姐妹,大家商量好了,輪流過來照顧”。
困境:欠的錢不知何日還上
午飯時間,記者從王詠梅的出租屋出來,找了一家拉面館。和鄰桌的顧客閑聊,得知很多都是慕名趕到上海來看病的患者和家屬。而就在拉面館不遠處的上海瑞金醫(yī)院,是他們僅存的希望。“如果這里也看不好,那就真的只能放棄了”。
說這話的是來自江蘇徐州的蔣新娟,她今年50多歲,但外表看上去要比她實際年齡蒼老很多。丈夫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吃著面,蔣新娟和記者聊起了自己的境況。據(jù)她介紹,自己和丈夫在決定來上海之前,其實已經(jīng)去過不少地方——揚州、南京等地,“那里的醫(yī)生推薦我們來上海看病,說這里技術(shù)好,不然我們也不會千里迢迢跑過來,而且我們是新農(nóng)合醫(yī)保,需要在屬地進行醫(yī)保,異地的話報銷比例就要下降很多”。根據(jù)蔣新娟的說法,目前像她這樣的新農(nóng)合個人醫(yī)保跨省就醫(yī)只能報銷三成左右,即便按照蔣新娟患的卵巢癌基本治療費用15萬元計算,她自己還要擔負10萬元以上,這還不算在上海看病期間和休養(yǎng)時所需的其他費用。
“在老家,已經(jīng)欠了鄉(xiāng)里鄉(xiāng)親好幾萬元了,咱們都是普通農(nóng)民,也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還上”,一旁的丈夫放下碗,對記者說,來上海看病,其實最大的動力就是給自己一個交代,“對咱農(nóng)民來說,來上海看病,如果這里也不行,那也死心了”。
| 下一頁 |

 分享到人人
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
分享到QQ空間












 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
 !
!